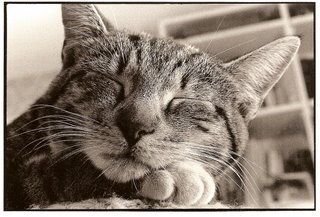空白
貓眼的世界:空白
台灣立報 2013/01/25
黃懷軒
如果可以什麼都不要思考,就好像一切都理所當然的那樣活著或許會是一件幸福的事。看著貓兒們趴在沙發上睡覺,就會覺得一切本當都該是這樣理所當然,思考這種傷腦筋的活動是人類發展出的獨家活動,一切美好燦爛與狗屁倒灶的大小事全都由此而來。一句猶太諺語說:「人們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因為我們越是想,答案就離我們越遠;越思考,真理就離我們越遠。
離開大公司的羽翼自行創業後,在台灣這條艱難的設計產業上一個人走,每天忙到快連呼吸都忘記了,這樣汲汲營營的結果,苟延殘喘的為了生活奔波,其實也就只能糊口,餓不死、富不了,幾乎沒了生活,每天就是被工作淹沒。每天從醒來就開始接不完的電話,聯絡不完的協調事項,無止境的無謂會議,除了折磨你的肉體之外,更加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一種心靈的折磨。我喜歡在工地鬼混,喜歡跟工人聊天,但我真的難以忍受那些坐在會議桌旁的「知識份子」。差距是什麼呢?就是這些能夠坐上會議桌的自認為高人一等、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人類總是認為自己才是有在用腦子思考的那個人;而在現場揮汗如雨忍受惡劣工作環境的工人們通常腦子則是一片空白。
我說的空白不代表做事不用腦子,而是一種思想上的乾淨與純粹。在工地工作的這群人,思想上絕大多數都是乾乾淨淨不帶雜質的人,不論是抽菸嚼檳榔或是滿口三字經LP來LP去,他們其實都沒有多想,一切都是出乎一種理所當然。即便是有時一言不和意見相左惡言相向,仍舊不帶惡意,像是出於某種本能的活著一般。現實生活的沉重壓力在他們眼裡也像是一種輕描淡寫帶過就算的必然,幹譙個兩聲就像屁一樣消失在空氣中就算了;高等人類的會議桌上就不是這樣了,所謂的思考絕大多數都是一種盤算,盤算著階級、職稱、地位、金錢、利益與權力,漂亮的話語包裝著一堆垃圾,充滿了髒污,臭不可聞。
幾年的忙亂下來,我的思考早已經污濁不堪。在著麼不願意盤算,為了糊口還是得搞髒自己。維根斯坦認為園丁是一份誠實的工作,跟聰明人談話是很「作賤心靈」的一件事(I prostitute my mind talking to intelligent people)。今早醒來,疲累的身體拖著疲累的心靈往另一個刑場走去。我想著如果可以的話,我願意用我現有的一切換取一種空白,沒有雜質的純粹,走回林子裡變回一隻純然的獸。
(展示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