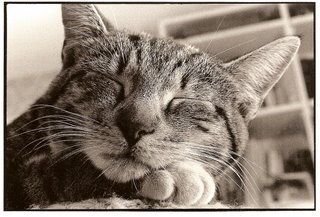博物館與脫衣舞
貓眼的世界:博物館與脫衣舞
台灣立報 2012/10/26
黃懷軒
小時候鄉下重大慶典或是廟會,有時連婚禮、喪事,都會看到電子花車。花車上本來只是說說唱唱,到後來狂歌熱舞,聲光四射,不知道是不是跳的真的很熱,台上的女郎們漸漸把衣服都脫光了。在我還很小的時候,淳樸的農村是很難想像這種事的,但到了我小學四五六年級左右,差不多到處都有脫衣舞可以看了。短時間內,民風開放之快、轉變之大,連我這自認適應力強的都市小孩都覺得不可思議。
達爾文提出的演化論說過,圍困在島嶼上的物種會發展出只適應當地環境的一種特化的樣貌、器官或是行為。我覺得脫衣舞是一種台灣非常獨特特化的民俗文化,許多人嗤之以鼻,但社會長期發生的一種狀態或行為終究會形成一種文化,也代表了某一個時代的氛圍。文化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只有還存不存在的問題,當某種文化消失了,也得看看消失的是現象或是觀念。當背後的觀念不在了,我們也才真的告別那個年代。我看,脫衣舞這東西,總有一天會在博物館裡展出的,只是不是現在,因為我們還是活在脫衣舞的時代裡。
現在的展示設計,每當談到一些比較「不光彩」(例如政策破壞環境、歧視、情色、災難等等)的內容時,不是輕描淡寫帶過就是乾脆刪了,因為不光彩,沒面子,說這些不好。但是不出現、不看、不聽也無法欺騙這世界,假裝這些東西不存在或是沒發生過。如果不是某種文化現象或背後的觀念已離我們遠去,我們永遠無法客觀地看待這樣一種內容。就像電視上播出的電影,露個屁股或是出現個糞便之類的也要打馬賽克,難道我們真的都這麼的純潔?看一下屁屁就會玷污我們高尚的心靈?
當到處有脫衣舞可看的表象逐漸消失,媒體卻悄悄的讓人們看脫衣舞的方式進化。低俗的媒體與無處不在的3C裝置,帶我們向聳動、情色、扒糞的方向一直前進,滿足我們窺探的慾望,口味越來越重。我們看輕一切重要的事物,只求在聲光色的世界裡痲痹我們的感官。就連博物館展覽的方式也常常因應電子化到一種不知所云的地步,展示故事線、空間設計其實都已退居第二甚至第三線,因為業主開宗明義就說要炫要酷,才能吸引參觀者。影音多媒體互動本身沒問題,適度的互動及聲光效果可以強化展示的效果。但其實是人有問題,無所不用其極地強化聲光互動,背後的思維也和電子花車沒兩樣。
如果展覽一直這樣搞還熱鬧滾滾,那我們肯定是還停留在那看脫衣舞的時代,一直站在台前沒回神。
(展示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