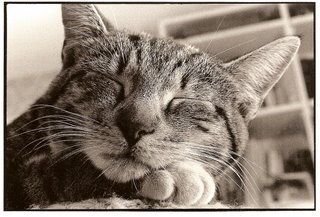所累何事
貓眼的世界:所累何事
立報 2012/04/26
黃懷軒
每當我感到疲憊的時候,我總會懷疑自己的工作現在究竟是在做甚麼?我時常感到自己在浪費生命,虛度光陰,我所在進行中的一切所謂「工作」,或攪和在這工作相關漩渦中的一切,似乎不曾出過一件好事,一件可令我感到問心無愧、輕鬆自在的好事。這種疲累的感覺,從我入行第一天就一直存在。我分不出是工作得太累讓我感到懷疑,或者是因為總是懷疑著所以才讓我感到疲累。
我們的社會機制要求你必須有工作才能求得溫飽,妄想如古人一樣離世索居遠離群眾在現代社會似乎是難如登天。即便你能夠放棄物質生活、金錢、名利,想找個安安靜靜的地方躲起來,除非是自己買塊地,不然山河森林不是屬於私人就是國家,要是效法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一樣躲到深山湖邊去蓋屋餵魚,不出三天肯定有警察來敲門把你帶走。世上的一切早已被瓜分得一乾二淨。
年輕時不懂事,年少無知,初學設計時以為我的使命就是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給別人,更好的居住空間、更好的享受,以及更好的生活。我們能夠就理論或是經驗重新設計空間,讓空間的使用更有效率、更加方便;我們也可以展現創造力與美感,透過材料的質感與細節讓空間舒適宜人甚至富麗堂皇。但事實上,更好的生活只會存在你的心中,實質的建築就某種層面而言並無法創造出那種東西,不論設計得再好、再精美、再昂貴。就像廟宇或是教堂蓋得再華麗壯觀其實都一樣,神怎麼會去住在那樣吹彈可破的東西裡面。
在中國工作的工地是個大得無法想像的施工現場,我們公司處理這一大片工地建築群中大約70%的室內裝修。工地面對著渤海灣,一望無際的汪洋,每當太陽落下,黃澄澄的夕陽泛著海面上的薄霧一起暈開,都會逼得我義無反顧的爬上鷹架去看它一眼。懸在鷹架上,眼前是令人窒息的美景,腳下則是一種像是世界末日般的廢墟景像。看著天上的飛鳥,不知牠們心中更好的生活是甚麼樣子?低頭看著踏著滿地碎石忙進忙出的工人們,不知他們心中想著的更好的生活是甚麼樣子?
忘了從哪看到或是聽到一句話,說是人一生不必想著要成就甚麼好事,只要能夠做到「無害」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站在鷹架上,腦子裡一直不斷出現這句話。人家說書讀太多會污染你的靈魂,想想真是一點都沒錯。
(展示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