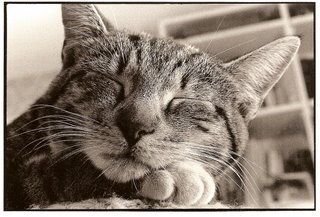差異(二)
立報 2012/03/29
黃懷軒
第一次遇見對岸的中國人是10年前,到英國的建築聯盟學院上暑期語言課程,當時中國人到英國留學的人不多。課堂上的討論很有趣,是我第一次瞥見專業上相對進步的世界。課堂上有各國人,中國同學是一對情侶,設計作品有點了無新意,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對設計有著強大的熱情。
幾年後我再到英國,接下來的求學生涯中我沒有中國同學,但英國早已滿是中國留學生。再一次接觸中國建築上的專業人士是最近這一兩年,和中國重要的建築學院合作幾個案子,業主都是建築學院的教授、副教授。在合作的過程中,他們對設計的想法常常是很制式的、有時也是很政治的,這大概是環境使然。他們的建築設計在公司內部的討論中被批評得很糟,因為他們缺乏實務執行的經驗,另一方面是工程的水準落差太大。不論結果的好壞成敗,來來往往的過程,我依舊看到了那強烈的熱情。
這群中國的建築人,專業上其實十分謙虛溫和,談論他們的設計時常常帶著一種靦腆的態度,好像自己作品上不了檯面似的,但其實他們都是畢業於全中國前五大建築名校中的碩、博士。他們期待你的回饋,討論務實的問題,沒有虛假的設計修辭;認真思考你提出的建議,並提出質疑。私下吃飯聊天,說東說西,談足球聊政治,他們思想開闊,有自信,對國際議題也有自己的想法,雖然他們身在一個相對不自由的國度,但心中的天空大得很。他們是中國的新生代。
在台灣,我們自視甚高,談到對岸總是或多或少的透露一種輕視,言談中帶有一種貶意,他們是鄉下人,不如我們,他們是「井底之蛙」。先別說中國在科技、工程等很多方面其實都已經超越台灣,也不談中國公德心普遍低落的現象;我只想說,其實對岸的知識分子相對的比較「真實」,所謂的真實,指的不過就是不虛榮也不自卑,不論是對他們的外在環境或是內在的專業知識,指的是一種感受能力,看見天空的能力。
在我們訕笑的「井底之蛙」國度裡,知識分子有專業的樣子,實事求是,對新的、比他好的,或說是超越他想像的部分,抱持著一種開放且尊重的態度。業界混久了,以專業者自居,但面對這種態度時常讓我感到心虛,在台灣的業界,常常都只看到一種墨守成規的態度,說的永遠比做的好聽許多,但又自滿不已。或許他們住井裡,但我們卻把井給戴在眼前,「以管窺天」的心態讓我們看小了世界,放棄了天空。
(展示設計師)
(展示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