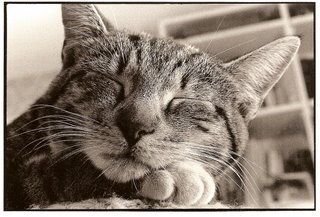只說愛,不做愛
貓眼的世界:只說愛,不做愛
立報 2012/02/23
黃懷軒
身為博物館展示設計師,我時常想著有天能成立自己的一座博物館,一座愛情的博物館。愛情是純粹的,或者不要說愛情,容易讓人誤解。關於情感,我想像它是純粹的。
想想「愛情博物館─Museum of LOVE」真是個很大的題目,有無限的可能。我可以設計個「名人之愛」當成常設展,以動物或小孩間最單純的情誼為開頭,闡明愛是我們的本能;接著來個現代的對比,說說八卦雜誌上明星名人情愛腥色羶的輕浮;再來回顧歷史,深入訴說如甘地、國父等古今中外歷史人物的民族情感;最後來個台灣政治人物的「愛台灣」大車拼之對比;從這些內容之中又可以延伸出許多不同主題的深入特展,我想一定會是個很有趣的博物館展覽。甚麼都可以成為展示的主題,俯拾即是。情愛本是一體,因為所有一切被認真對待的人事物,都脫離不了愛情的範疇。
所有的愛,說穿了不過就是「在乎」而已。親情、愛情、友情或是對某種事物的熱情,這些其實都與現實無涉,唯一指涉的只有個人。當我們面對情感時,一切的外在條件都將消失,道德也好、輿論也罷,都將無足輕重。一個工人在乎他做的一切,那他終將成為一個匠師;一個政治人物在乎他訴說的每一個理念,那他終將成為一個政治家。在乎你的工作,在乎你的言行,始終就是一種愛情。
現在大家只說愛,卻不做愛,當然更不活在愛裡頭。成天說著滿嘴漂亮話,在網路世界按讚、匿名留言,或以道德之姿出來呼籲東呼籲西的,其實只是為了某種關於現實利益或名聲之類的東西所做的「表演」,與愛無關。如同政客名嘴成天掛嘴上的「愛台灣」,充其量只是一種「口愛」,爽完就沒了,因為他們言行並非如是,因為他們並不活在其中,不是真的在乎。
人人討厭小三,自從甚麼偉大的人妻偶像劇出現後更是如此。但在某種程度而言,我反而尊敬那些「小三」,因為起碼他們敢面對他們的情感並為之拋棄現實。跟政客與偽君子比起來,小三們簡直偉大的不得了。我不是鼓勵大家去當小三,而是對比起來,實在很受不了台灣社會上這種普遍存在於各種公、私領域的不當真、不在乎的輕浮氣氛。
博物館以教育為目的,說教育太偉大了,我只希望我的博物館可以呈現出一種重量,一種在乎,一種「愛情」的世界。在日內瓦通往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會博物館路上的樹林裡有一座甘地的雕像,座上刻著「My life is my message」,對於生命與情愛這種東西,我無法說的比他更多了。
(展示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