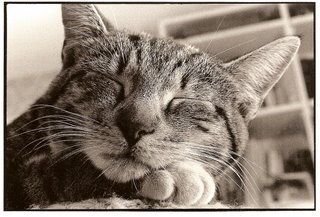新聞不好玩
貓眼的世界:新聞不好玩
台灣立報 2013/03/29
黃懷軒
好不容易忙完,坐下來迎接我饅頭配咖啡的第一餐,打開電視不小心看到新聞節目實在是令人感到很痛苦,餓了一天不想連饅頭都吃不下,不消30秒一股怒火又冒上來,趕緊轉台。
亂轉一通看到電影台在播個和新聞有關的電影(還是影集?),突發新聞有某個國會議員遭到槍擊,整個新聞團隊一陣忙亂,訊息也很混亂,新聞播到一半其他各大媒體紛紛報導該名國會議員已經死亡,但是由於訊息來源無法證實於是新聞團隊決定不跟進報導。某個高層質疑他們為何不報,團隊裡負責查證的人說:「那可是一個人,宣告死亡是醫生的事,不是新聞媒體的事。」最後證明只是謠言,該名國會議員還在進行手術。再寫實的電影情節畢竟是虛構的,但其實也反映一種理想狀態。
小時候不懂什麼叫做新聞,也不懂記者這個職業到底是做什麼的,更不了解這些到底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只覺得新聞真是一種無聊的電視節目,一點都不好玩。小時後第一次對新聞記者這東西有所瞭解其實是來自一部香港電影《神行太保》,片中記者對新聞專業的熱情、對真實報導的執著讓我覺得新聞記者真是一種了不起的職業。小孩嘛,電影嘛,總是參雜了許多想像、憧憬與理想。
兩相對照起來,小時讓我感到無聊的新聞節目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反而像是珍寶一樣在台灣現在的媒體生態中不復存在。現在的新聞節目做得比娛樂新聞還精彩,血腥、叫罵、哭喊、露奶、美食加搞笑,內容豐富不一而足。遇到重大刑案的時候還會兼做警探與檢察官甚至法官,帶你抽絲剝繭追追追,來個莫名其妙兼一點可信度都沒有的什麼深度報導,但基本上大概就只是一連串的臆測與扒糞而已,毫無新聞價值不說,連對被報導對象(不論是受害者或嫌疑人)的基本尊重與保護都蕩然無存。
新聞報導的價值在於資訊的給予以及正確性,任何臆測與誤導都會造成傷害,不該是一種兒戲般的隨便。就某個層面而言,用一種審慎認真的態度做好你的工作就夠大恩大德了,沒人要求更多。新聞不需要情緒,媒體不是法官,新聞節目也不需要好玩,如果新聞媒體認為好玩有趣具備娛樂效果才能被群眾接受,那其實代表我們的社會原來還在喝奶的階段,幼稚的不得了。
(展示設計師)